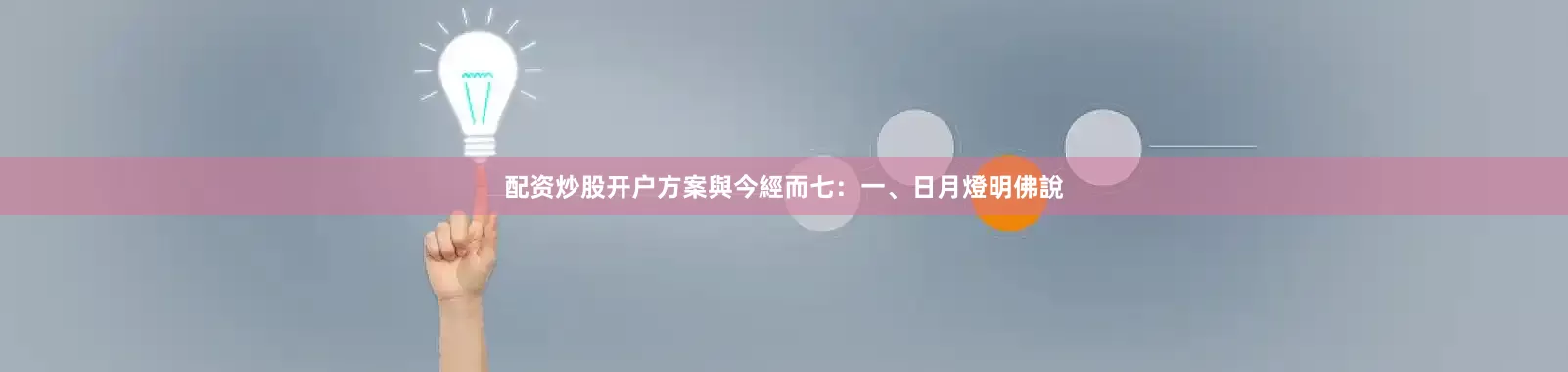
發大心文
震旦苦惱眾生某,稽首盡十方三世諸佛前:伏以人身難得,佛法難聞,我今得少善力,得生人中,正像雲遐,末法現在,欲報大恩,須發大願,依經論說,行是車船,願是馬楫,有船無楫,難可到也。我自諸劫以來,佛加被我,佛教誨我,佛憶念我;我有眼根不見,耳根不聞,意根不覺,流轉生死,旋出旋沒,至於今生,今生更遲,何生可待?父母生我,善友教我,一世有情,鹹加被我,況自諸劫來,若父若母若眷屬,或生天中,或生人中,或生畜生中、地獄中;我若不以今生坐大願船,自鼓願楫,盡諸後身,終成蹉忽,負恩無極,是謂枉得人身,虛聞佛法。是故欲修檀者,發心為先;欲修羼提,發心為先;欲修屍羅,發心為先;欲修毗黎耶,發心為先;欲修禪那,發心為先;欲修般若,發心為先。我今先願斷種種心。何謂種種心?瞋心差別有三:曰嫉惡心,曰怨懣心,曰難忍辱心。貪心差別有三:曰樂世法心,曰羨慕心,曰憶世法心。癡心差別有五:曰善感心,曰纏綿心,曰疑法心,曰疑因果心,曰惛沈心。有境相應行心,有非境不相應行心;若廣分別言,則有八萬四千塵勞,皆起一心。我今誓發大心,凡生人倫,受種種惱,大心菩薩深知因果,各各有故,略可設說。脫令我今世適發善念,欲入正受,即有魔事,不得成就,便當知前生善根微淺,嬈善友故。脫令我今世出誠實言,而以訴人,人反譏笑,便當知我前世信根微淺,不聽它言故。脫令我今生多受浮言,無情淺夫,或用見成言說而成謗論,便須知我前世處境亨泰,但能坐議,不察人世一切真實煩惱故。脫令我今世於人有禮,人見淩侮,便須知我前生忍辱根淺,或加報復,或喜我慢,今回報故。脫令我今生如孩如提,純取真初而以待人,人相機詐,受種種惱,便須知我前生閱曆太深,厚貌深中,今受報故。脫令我今世既招謗議,復值嫌疑,難可解說,便須知我前生坐於堂上,身為理官,但據形跡故。脫令我今世自細及巨,萬事萬狀,不得擇術直行,如頭欲前而足欲後,便當知我前生直截如意,平生處置,數言可了,不知它苦故。脫令我今世進身坎軻,橫見貶抑,便須知我前生僥取榮利,貪賂罔法,不畏人王,不恥姍笑故。脫令我今世種種處置,雖竭仁智,終無善局,便須知我前生害他眷屬,累其一生故。脫令我今生於世間愛樂,百求無遂,凡所施作,垂成忽敗,便須知我前生於它若有仇若無仇,一切破壞故。脫令我今生遇有惡緣,未可明言,便須知我前生誤作媒翳害它人故。脫令我今世受無量冤讒,無量憂泣,不可明言,便須知我前生順遂享福過故。脫令今生遇凶人暴辱,如豺虎行,便須知我前生無禮以淩人故。復次諸佛,我若後身仍生人倫,或生此世界,或生餘世界,依雜華普賢說,東南西北世界,東西南北四角世界,上方下方世界,乃至盡毗盧遮那海世界,皆當發心而正思惟。如遇它橫逆,應正思惟,生安受心;遇它機械,應正思惟,生憐他心;遇他作惡,應正思惟,生度他心;遇他冥頑,不忠不孝,不存血性,於家於國,漠然無情,應正思惟,生感動他心;遇他遏抑我,噬負我,皆正思惟,而生憐他心;遇他頑癡,應正思惟,生敬他心;遇它妒忌,生讓它心;遇它醜惡,應正思惟,生愛它心;乃至見他十惡五逆,亦將我心置他胸臆,而替他想,生種種憐他心,宥他心,度他心,乃至一切施不如願於我,我皆如是思惟,此我夙業,今生幸已受報,已償已訖,生自慶幸心。
復次:諸佛,我若後身仍生天倫,若日天子,若月天子,若星辰天子,或生忉利天,或生須焰摩天,或生四天王天,或生它化自在天,乃至生諸梵天,乃至生五不還天,生色究竟天,皆當發心,憶見眾生,照見眾生。我生天上,入於內院,值補處佛,佛已降時,最先請佛說法,佛涅槃時,受我最後法供,如純陀事,佛佑第一,當念世人不值佛世,或又遭遇滅法人王,我皆衍佛法緒而以度之。我生天上,身有千頭,頭有千舌,舌有千義,氣足音宏,辯才第一,當念眾生冤枉蹇澀,若忠臣,若孝子,若賢婦、孝女、奴僕,種種屈曲繚戾,千幽萬隱,我皆化身替他分說而以度之。我生天上,威德自在,尊嚴第一,當念眾生賤苦而以度之。我生天上,寂然安隱,得諸三昧,陀羅尼門定慧第一,當念眾生或困色陰,或困想陰,種種顛倒,我施安隱而以度之。我生天上,壽命第一,當念眾生朝有夕無,哭泣相續,我施壽命而以度之。我生天上,安居第一,當念眾生或涉大水而困濤波,或從高山跌落,不得至地,心怖神飛,我當化身空中,為其接住而以度之。我生天上,調適第一,當念眾生生惡毒瘡,種種苦病,或遇刀刃,或落半頭時,或斷手腳時,或刳腸胃及兩眼時,求死未死時,我皆分身而以度之。我生天上,潔淨第一,當念眾生在於地獄,既受無量痛苦,仍在沸屎,受無量穢,我皆不憚親往而以度之。我生天上,慧照天人,多聞第一,當念眾生少見寡聞,於一切處自疑自駭,我當令其到心皆平,而以度之。我生天上,久遠超出因明、內外五明,神明第一,當念眾生小聰小辨,世法多聞,或困名身,或困句身,或困文身,顛倒日夜,我先化身令其成就,然後解脫而以度之。我生天上,春吐栴檀氣,夏吐芬陀利氣,秋吐蘭氣,冬吐須曼那氣,身長由延,端正第一,當念眾生現富單那形,鳩盤茶形,夜迦形,或人生中粗弊如畜,福力輕微,或生疣贅,五官不全,同倫譏厭,己亦厭苦,我當巧術而以度之。我生天上,八萬四千微妙侍女,來相親娛,著微妙衣,出微妙聲,或以攜手為極樂,或以相笑為極樂,當念眾生困於粗重欲,不知厭苦,復有慧根男女,想陰熾盛,生諸疾病,種種粗細境界,我皆化作色身,為其成就如願,然後解脫而以度之。我生天上,供養第一,當念貧窮眾生,我以法力取龍宮寶貝,或美衣食,而以度之。
復次:諸佛,我若度人,當發大願心,先度此生父身、母身、眷屬身,再度曠劫以來,不可說、不可說、父身、母身、眷屬身;又當度此世一世知識我之身,又當度曠劫以來,不可說、不可說、識知我之身,又當度曠劫以來至於此世,與我有仇、有怨之身,乃至遍度曠劫以來,至於今世,若因緣,若增上緣,若等無間緣,若所緣緣,若有情而作緣,若無情而作緣,人所不見天眼乃見之身,依《首楞》說,十二類生,各各入其類中,而說法要而化導之。雖有化導化身勞苦,我實寂然,不出於定,安坐本所,不離三昧,身心如故。凡此所願,我實誓發,無虛誑心,所願佛加被我,佛證知我,佛提撕我,佛成就我,使我盡此一形,乃至千形萬形無量形,盡諸後有。無凡夫障,無小乘障,無中乘障,無外道障,無魔民障,無魔王障。正念相續,正願相續,正知相續,正見相續,正行相續,我盡諸身,若毛發,若肝腦,若頭目,而以作供,不作為報。我雖化身,橫盡虛空,豎盡來劫,作其塵沙,一一沙中,有一一舌,一一舌中,出一一音,而以讚佛,不能盡也。又以化身,豎盡來劫,橫盡虛空,作其塵沙,沙中一一舌,舌中一一音,而以勸人讚佛,不能盡也。世界無盡,佛力無盡,眾生無盡,一世法無盡,我願亦無盡。
〈(癸未夏,余編初集二百二十篇竟,其正集九十又八篇,以此文竟。過是以往語言文字為《定庵二集》。自記。)〉
重刊圓覺經略疏後序
《唐書藝文志》曰:「《圓覺經》大小疏各一卷,釋宗密撰。」裴休《圓覺疏序》曰:「凡《大疏》三卷,《大抄》十三卷,《略疏》二卷,《小抄》六卷。」今藏本疏與抄皆合,不各自為本,《大疏抄》合十二卷;《略疏》二卷,各分上下;《略抄》或十二卷,或二十五卷;多寡之數,析省之年,皆不可考矣。《圓覺》之為圓覺,我佛自言之;《疏抄》之為疏抄,圭峰師自言之。夫賦天地者迂,讚日月者妄,名字功德,吾無贅言。若其祖荷澤,禰遂洲,則傳法之緒可言也;胎慈恩,息賢首,其講經之宗可言也。大疏雖繁,不可謂多,略疏雖簡,不可謂少。其二而一者,同是經之津筏;其一而二者,各具疏之體裁。茲取《略疏》契之,使學者先讀是,次第尋求也。《唐誌》又曰:「《禪源諸詮集》一百一卷,《起信論疏抄》三卷,《原人論》一卷,皆宗密撰。」裴休撰樂石之文,舉師所箸,有《華嚴》、《圓覺》、《涅槃》、《金剛》、《起信》、《唯識》、《孟蘭》、《法界觀》、《行願》等經論疏抄,及法義類例,及禪藏總九十餘卷。以今藏,佚者半,存者尚半。今先取《圓覺》契之,亦使學者先讀是,次第尋求也。契之者誰?吳縣貝居士墉也。助之喜與與其役者誰?吳縣江居士沅及仁和龔自珍也。道光四年八月朔龔自珍合十,說由緒竟。
助刊圓覺經略疏願文
大清道光四年,佛弟子仁和龔自珍同妻山陰何氏敬拾淨財,助刊《大方廣圓覺修多羅了義經疏》成,並刷印一百二十部,流傳施送。伏因先慈金壇段氏煩惱深重,中年永逝,願以此功德,回向逝者,夙業頓消,神之淨土。存者四大安和,盡此報身,不逢不若。命終之後,三人相見於蓮邦,乃至一生補處。
為龍泉寺募造藏經樓啟
大法之東也,寄囑人王,寄囑宰官、長者、居士。予讀全藏,有官譯,有官寫,有官判,其目錄盡在官。宋藏、元藏,今頗有存者,皆官紙,紙尾有官牒。其世近尤易徵者,永樂中詔刊全藏一萬一千餘卷,依周興嗣千字臚而次之,頒天下諸寺。今在大江以南者為南藏,在京師者為北藏,香木銅鐶,象玉錦繡,以為裝函;高樓飛宇,以為庋閣;名稱歌曲、香火之田,以為讚歎、護持、供養。明祚久長,十五陵巋然。明之士大夫,席承平之清暇,往往探秘典,問玄文,支那盛有述作。萬曆中,浙之徑山,始易梵夾為冊書,別刊經論五千卷,剞劂浩穰,亦問之一時士大夫。予讀徑山藏,識其卷尾,考其出貲之家,盡科目之選,而誌乘之傑也。垂三百載,其雲礽遺裔,多豐饒貴顯未艾者,功德吉祥,豈其誣乎?微獨往古,我世宗憲皇帝,神聖天縱,留意內學,謂是與周孔之言,異名同實,不可執一廢一者也。爰頒大帑,契眾經二十八種,合二百餘卷;又刊《古德祖師語錄》三十八種,百餘卷;又刊《宗鏡錄》百卷,頒諸寺。又詔以潛邸之雍和宮為奉佛處,以大臣專領之。高宗朝,益置內府匠人其中,月塐象三百尊,離世勿減,其象歲頒京師諸寺。自法流此土,功德無如聖清者;國祚世運,自有書契,則亦無如我聖清者。通儒大方,可以篤信,可以力行也矣。」夫有倡於上,則必有貴種福德之臣助於下,相與報佛恩,祈福德,以合成一世界之福德,豈可闕也?永樂北藏全千函而不缺者,今茲僅矣。京師九門,不滿三十分。宣武門西南龍泉寺,古刹也,實有一分,完不蝕,望之櫛然,觸之馤然。寺卑濕,慮其久而蠹也,無樓居,慮不足以極崇弆之美也。且龍泉地勢清遠,水木之表,宜有鬱然靉然者峙焉,使民望焉為祈向之宗,百福之彙,而以庇國庇民,不亦美乎?王公貝勒,貴官大夫,無使徑山專美明代!
誦得生淨土陀羅尼記數簿書後
龔自珍以辛卯歲發願:願誦大藏「貞」字函《拔一切業障根本得生淨土陀羅尼》五十九言四十九萬卷,願秘密加被,滅我定業,疾證法華三昧。上品上生,生阿彌陀佛常寂光土,限戊戌歲畢之。又為之記數簿,書其尾曰:威儀不二門,若行則誦,若立則誦,若坐若臥則誦。聲音不二門,古譯音不準,既辯之矣,予能肖彈舌,依今譯大攝小,亦能以大攝小書,然而不廢古譯。夫不知今譯而至心持古譯者,如麻似菽,責譯主可矣,豈虞持者之不靈,與我佛之不委曲聰聽哉?願不二門,予有本願十焉,一願中具有九願,九願中一一有彼九願,如環無端,如黃鍾旋相為宮,如牽一發,全身知覺,杜順師《漩複頌》曰:「時處帝網見重重」者也。自它不二門,予誦咒時,觀恒河沙眾生,無一眾生不同時誦此咒者;恒河沙世界,無一色一香非此咒相貌者。挹注不二門,予所有持咒功德,往往觀想用施一眾生,亦用施恒河沙眾生,於我功德,不增不減。老子曰:「既以與人己愈有,既以為人己愈多。」《天台四念處》第四卷曰:「不積藏。」予稟此旨時,不二門初發心時,未誦時,已滿四十九萬卷。數不二門,一一卷中具有四十九萬卷。心法卷不二門,或心係佛,或心係願,或無心,或用一切處心。一切處心可用乎?應之曰:飛錫師曰:「盡大地以為的,烏有箭發而不中者哉?」顯密不二門,此陀羅尼即一切陀羅尼,誦之即是誦大小《彌陀》諸經,即是誦《法華經》,亦即是誦一切經,十方三世佛經。教相不二門,佛言法華三昧,即是言上品上生也。華果不二門,此方為華,西方為果;此生為華,生彼為果。十方不二門,如天台智者大師說不可具說。三世不二門,如天台說。心佛不二門,如大勢至菩薩說。
雙非雙亦門頌
昔龍樹菩薩作《四不偈》,六祖大鑒大師作《識智頌》,杜順和尚作《漩複頌》,宋瑩中大師作《三千有門頌》。予讀天台師《覺意三昧》竟,發明之,乃製《雙非雙亦門頌》,頌曰:既雙遮,那雙照?先遮後照,拖泥帶淖。既雙照,那雙遮?先照後遮,忙如亂麻。遮墮三句,照墮四句,墮三四句,那有是處?離三四句,別無言句,佛依二邊,我依四句,謗佛謗我,莫謗龍樹。破者立之,立者破之,即立即破,我無兩時。你謗你捉,是思議境,不思議境,豈複立境?我不立境,我無凡聖,你今說空,所空何物?囫圇現成,雙非雙亦。天台龍樹,龍樹天台,大事出現,佛知見開。
附:重定雙非雙亦門頌一首
丁酉九月二十五日,天將曙,夢梵僧告予:龍樹因緣偈,須以一口氣急讀之,不得擬議。既寤,取筆改定舊所製頌。是為《重定雙非雙亦門頌》。 捉雙遮,放雙照,先遮後照,拖泥帶淖。捉雙照,放雙遮,先照後遮,忙如亂蟆。立者破之,破者立之,即破即立,無呼吸時。遮墮三句,照墮四句,我墮四句,我無是處。你離此句,別無言句,滑達失步。佛依二邊,我依兩句,謗我謗佛,莫謗龍樹。你謗龍樹,謗一切處,我禮龍樹,禮一切處。你捉一境,道有凡聖,我捉一境,是不立境。我不立境,聖凡凡聖,道我捉空,空何等耶?空受我捉,何所本耶?現成現成,囫圇囫圇。天台龍樹,龍樹天台,大事出現,知見華開。
正譯
第一(正《法華經》秦譯)
《妙法蓮花經》入震旦之一千四百四十四年,為大清道光之丁酉歲,龔鞏祚始正之曰:譯者誤也。誤奈何?曰:此書實二部,各有序、正、流通,合並之,誤者一。前經十品,後經十一品,無二十八品,今二十八品,其七偽也,其一別行也,誤者二。二經各有蔓衍,後經尤雜糅,譯者不察,誤者三。顛倒失其次,移《安樂行品》於後經之中間,誤者四。移《囑累品》於《藥王普門》諸品之上,使已沒之寶塔複有言辭,使未離佛側之文殊來自大海,疑惑眾生極矣,誤者五。又告之曰:第五事,晉譯、隋譯不誤。
正譯第二(正《大品彌陀經》魏譯)
或問龔鞏祚曰:《阿彌陀》四十八願有之乎?龔鞏祚曰:蛆蟲師之言也,若非蛆蟲師之言,則譯者為之。昔者法藏比丘之發願也,有本有跡,有理有事。本也者,泯一切數,立一切數,一數攝無量數,無量數入一數。若十方,若過去世,若見在世,若未來世,無一色非我願者,無一香非我願者,乃至若地,若水,若火,若風,若耳,若眼,若鼻、舌、身,若意,若我願,若它願,無非我願者。是故我願實不可得;是故我願實無有數。盡十方眾生皆成阿羅漢,測量卜度,欲照明其數,終不可得,如其跡則必有定矣。我在西方,非東,非北,非南,亦非四維,亦非上下。成佛以來,十劫而已。非一劫、二劫,乃至九劫,亦非多劫。娑婆眾生,不感我說,釋迦代說。自說其跡不定,法藏誑眾生矣,代說之不定,釋迦誑眾生矣,結集之者書其數不定,阿難誑眾生矣。梵冊貝葉,以意增損,以意排比,以意合之分之,譯者從而受之。《大藏》所見,或以四十八願,或以三十六願,或以二十八願,或以二十四願。四十八願,獨見流通,乍聾乍眩,詎可信受者乎?
正譯第三(正《大本彌陀經》)
問:依魏康僧鎧譯四十八願,何不可也,詎知非眾生因緣,當信受是四十八願也哉?答:不可也。我為一一正之如左,盍平心察文義矣!
第十七願,衍文也。十方諸佛說經行道之跡,各各不同。眾生因緣不同故,非佛有優劣故;乃言十倍於諸佛,為是十倍誰耶?第二十五、第二十六,隻是一願,非二也。
第二十八、第二十九、第三十願三段,可並入第二十七願中。第三十一願,可並入第二十三願中。
第三十四願,衍文也。我刹中人欲生他方,前文明其本願矣,乃慮墮三惡道,此義不必宣矣。第三十五、三十六願,皆可並入第二十二願中。第三十七願、三十八願,隻是一,非二也。
第四十一願,衍文。為道場樹耶?道樹不必當一願;為菩薩知見耶?菩薩知見,具如上文矣。第四十四願,衍文。具見上文,且疊見矣。
第四十五、四十六、四十七、四十八願凡四段,隻是一,非四也。然則法藏本願如何?曰:佛有願而已,不臚願之數也。
正譯第四(正《彌陀經》)
凡淨土眾經各各異,發願多少異,予揭之矣。有明袁居士為《西方釋異篇》,有身城大小異釋,有壽量多少異釋,有花輪大小異釋,網其眾說,彌縫同異,可謂勤矣。予乃正告震旦曰:不足辯!凡言大小、高卑、延促、多寡之數,十九是西竺注疏小師依托為之。一切經預設架構,言一、言二、言三、言四、言五,乃至言八萬四千,此方師筆之書,為《大明三藏法數》篇,以非佛口親說,是以處處異。又凡言若干那由他,若干恒河沙,若由旬,若劫,若國土,十九以意增益,氣喘詞窘,無益至教,亦處處異。佛言豈若此其絮絮猥鄙如兒女子語哉?五痛五燒,最不詞,《寶積經》中無量壽如來會,無是文也。若金口親宣,曷為有譯有不譯?於正是譯也,發其凡焉。
正譯第五(正《大般若經》)
龔鞏祚曰:唐玉華寺譯《大般若經》六百卷十六分,是西土偽經也。第二分,用秦譯《摩訶般若波羅密經》,又模擬此經造四百卷,立初分,又模擬此經造百餘卷,立第三分、四分、五分、六分;又取此經餘滓,造數十卷,立第七分,至第十六分。獨第二分是真經也。何以明此真?曰:龍樹大士依此造論也。真經不恃唐譯,鳩摩羅什、僧叡兩大師,先勒成三十卷九十品,流通震旦矣。西土如別有六百卷者,龍樹不應不言,羅什不應不見。且夫《摩訶》者,大也,三十卷九十品,已得一稱,無容更有繁於此,更得大稱者。蓋判教諸師,判立三宗,中西並然。相宗、性宗,卷氎繁重,此師習此破相宗,欲敵餘宗,恨文不富,門戶小見,漸至僭偽。豈知教縱分三,佛止一佛,矧教縱分三,豈必卷氎相敵,始成三峙耶?龍樹大士依三十卷九十品文,作《釋論》一千卷,又名《大智度論》,羅什存一刪九。龍樹之言,圓賅三藏十二部教,不專詁破相。又龍樹借此經,廣明三藏十二部教,不專執破相。又龍樹《釋論》論也,十倍原文,體裁可爾,秦二師尚以為廣而刪之。唐師乃以經為略,又取西土偽經而譯之,唐師所見,遜秦師遠矣哉!唐圭峰大師曰:「《般若》諸經,一氣數百非字,一氣數百不字,一氣數百無字。」夫佛一代時教,立此一門,顯此一境,標此一諦。判三宗者,是破相攝。判三乘者,是大乘攝。判四教者,是別教攝。審三諦者,是真諦依止。修三止者,是體真止依止。修三觀者,是空觀依止。發此音聲,有此卷氎,有此言句矣。此言句者,不同相宗之艱言,不同性宗之辯言,不同小乘經之確言,不同陀羅尼之密言,不同伽陀之文言,最易剽竊,最易模擬,敷衍萬倍,登龍宮之華嚴。求其後義,仍是前義,造作何難?然且校量功德,倍其文焉,然且廣明罪報,恫喝挾製,又倍其文焉,使人敢怒而不敢議,我佛豈有是哉?使圭峰知予說,早唾置之矣。乃辟喻說之曰:佛說般若,醍醐也,模彷附益者,水也;醍醐一滴入一缽盂水,水多醍醐少矣,乃至入七缽盂水,水益多醍醐益少;《大般若》六百卷,是取醍醐一滴,入四大海水。
正譯第六(正密部、正偈頌)
龔鞏祚曰:夫稱理以況,簡及苕帚;就事以詮,則有密部。密部所貴者,聲而已矣,聲所貴,輕重分寸間而已矣,輕重分寸間,在乎正音與帶音之間。正音宜大書,帶音宜旁書,二合以濟聲之窮,三合以濟二合之窮,四合以濟三合之窮。今回部語用彈舌音,乃至五合,其宜以大字攝細字書。譯師無知,用一律書,間用二合矣,而無三合四合,無三合四合,故密部不符佛口,密部不符佛口,故理一事二,疑惑眾生。聖清控馭天竺額納特珂克之地,達賴、班禪額爾德尼、章佳胡士克圖,先後來朝,世宗、高宗命譯諸陀羅尼以進,爰肖其音,用大攝小,書之鏤之,藏板雍和宮,印行以賜天下諸寺。偉矣,邁矣!天龍鬼神八部嗬護,在此不在彼矣。且夫西竺之國,威儀文詞之美,古德慕之。凡見佛者,則有唄偈、樂器讚頌;問佛谘義,往往用偈頌。佛說法畢,則有重宣之頌,如東土之有歌詩諧聲者也。中西聲不同,不可以諧,不如勿譯;譯焉而拙直,無唱歎之旨,徒複正文而已,不如勿譯。震旦人造偈,沿彼譯師,承厥訛謬,截割字數,俾就整壹,若四字,若五字,若七字,不葉韻,中西皆無此律令,不知何名,鬛耶角耶?文筆之鬛耶?
正譯第七(總正曆代所譯一切經)
釋迦牟尼之興也,有語言,無文字,有付囑法,無付囑經。釋迦既沒,阿難結集釋迦一代五時之教,五味以判,三藏以位,十二部以分,經之名以起。如是者何也?謂自法也。我,阿難自我也;聞,阿難自聞也。某品某品,皆阿難所定也,阿難不得以記事記言之我,而僭曰佛也;亦猶佛不得預攘記事記言之阿難,而誣曰我也。今之經凡雲佛說,是經時追稱之詞,謂之小不辭;凡雲佛說是其品時,謂之大不辭;亦有問答未竟,佛遽唱言持此經功德、謗此經罪報者。日中相不應見日入相。湣哉!西竺既尊佛,國王貴官長者皆事佛,其以名聞相高,必在佛經焉;利祿之門,必在佛經焉;由是門戶之爭,朋黨之立,亦必在乎佛經焉。由是人尊一經,經立一師,家抱一冊,戶名一偈,各立原委,各造文字,或損改,或顛倒,或附益,猶不售,則又加之以恐喝挾製,校量罪福。罪福之文,十倍其原文矣。由是各經流通分,各各自名經中之王,序分各各造法會,各各名無量會;此文又三十倍其正文。佛清淨誨,汩沒其中,若存若亡,其言有曰:如遇持是經者,出其過惡,若實若不實,此人現世得白癩病。此其言為是佛言,為是持經者言,尚待問耶?佛言:「我如師子王,一切無畏,畏師子身自生蛆蟲,食師子肉。」(吾本是訓,名之蛆蟲僧。)譯主不察,盡譯之以貽震旦,震旦之謗佛,譯主之咎。
妙法蓮華經四十二問
第一問:三藏十二部,《妙法蓮華經》為經之王,何也?答:隋以來判教諸師,皆曰《華嚴》日出時,《法華》日中時,《涅槃》日入時。明藕益大師曰:「諸經有《法華》,王者之有九鼎,家業之有總帳簿也。」與一切經各各自言經中之王不同,欲備知之,則在《天台玄義》矣。
第二問:是經紀事多於記言,何也?答:明幽溪大師曰:「是經說綱不說目,說意不說義,一切經所說,統於是經說。」是經所說,則有三焉。何謂三?一、不說之說,二、正說之說,三、辟喻說之說。放光示瑞,天雨四華,地六種動,此不說之說。方便品說一大事因緣出見於世,說我但一乘,尚無有二,何況有三?此正說之說。以下乃辟喻說:一、《火宅喻》,二、《藥草喻》,三、《化城喻》。且說法,且授記,《法華》第一會畢矣。
第三問:此經應作何科判?答:吾初讀《法華》白文,審是二分;及見智者《文句》,果判二分,大喜曰:凡夫知見,乃與大師暗合。又讀七周,乃言曰:智者《文句》,大綱舉矣,條別未盡也。吾大意符智者,別出科判,自《序品》至《學無學品》訖為一會;以《安樂行品》為流通,自《見寶塔品》以至《妙莊嚴王品》為一會;以《法師功德品》及《囑累品》為流通。
第四問:如子之言,兩部各別行可矣。答:如是。
第五問:問其目。答曰:《序品》第一,《方便品》第二,《授舍利弗記並說火宅喻品》第三,《須菩提迦葉等說窮子喻品》第四,《藥草喻品》第五,《授迦葉等記品》第六,《說大通智勝如來並說化城喻品》第七,《授五百弟子記弟子說衣珠喻品》第八,《授學無學人記品》第九,《安樂行品》第十,以上《法華經》第一會竟。見《寶塔品》第一,《授提婆達多記龍女獻珠品》第二,《從地湧出品》第三,《如來壽量品》第四,《常不輕本事品》第五,《藥王本事品》第六,《妙音菩薩來往品》第七,《普門品》第八,《妙莊嚴王本事品》第九,《法師功德品》第十,《囑累品》第十一,以上《法華》又一會竟。
第六問:何以刪《法師品》?答:辨士之虛鋒,墨士之旁沈。第七問:何以刪《持品》?答:無意義,非佛語。 第八問:何以刪《分別功德品》?答:凡校量罪福,最繁重。閑文之諄,三十倍於正文,非佛語也。第九問:何以刪《隨喜功德品》?答:同上。第十問:何以刪《如來神力品》?答:無實義。
第十一問:陀羅尼可刪乎?答:一切經陀羅尼,皆宜別行在密部,於此經發其凡。
第十二問:何以刪《普賢勸法品》?答:偽經之最可笑者。凡恫喝挾製之言,皆西竺蛆蟲師所為也。(詳《正譯第七》。)又此經自有《囑累品》,不容益此品。
第十三問:何以移《安樂行品》於前經之末?答:以文殊始,以文殊終,說《髻珠喻》以申前三喻,經之首尾如是矣。陳南嶽大師以此品別行,有《玄義》一卷。
第十四問:何以移《法師功德品》於後?答:依智者師,此品譚神通名發得通,是說果,非說因也,宜入之流通。問:何以知是後會之流通,不是前會之流通?答:前會不以神通為流通,此多寶佛所被譏耳。
第十五問:何以移《囑累品》於最後?答:晉譯如此,隋譯亦如此,獨秦譯不然。依晉隋兩譯以正秦譯,不亦可乎?此一端可正全經之顛倒竄亂,非阿難原文矣。又此品佛明言多寶佛塔,遷可如故,法會遂散,而下品《藥王品》中多寶佛讚宿王華何哉?《普門品》中觀世音以一分瓔珞供多寶佛塔又何哉?其倒置不屑辯矣。
第十六問:今本大錯亂安在?答:文殊師利在八萬菩薩上首,彌勒問焉,未離佛側。《提婆達多品》佛留智積云:「且待須臾與文殊相見。」文殊乃與無數菩薩自龍宮湧出。不識文殊以何時入海耶?後經更端與前經不相承,別為首尾,不待深明文義者察之矣。
第十七問:願聞第二會何為而作?何人所作?何時所作?十一品之中,大綱細目,脈絡所在,首尾之指,可得而覼陳乎?答:阿難作。其時在授《三根記》訖以後,久遠矣!其文以多寶佛為主,以塔見塔沒為首尾;又以下方海眾為由緒,以如來壽量為正宗,如智者大師說。又十一品中龍女也,藥王也,常不輕也,妙音也,觀世音也,妙莊嚴王也,此六人者,皆證明如來壽量者也。以六重證明之,以六番指點之,以六事敷演之,以前經例之,此皆不說之說。如來壽量,是正說之說。又第十一品亦名《多寶塔滅品》,多寶佛為證明之始,為證明之終。
第十八問:何以言《藥王品》有蔓益?答:較量罪福入此品,不倫最甚也。
第十九問:仁言有非阿難原文者何也?答:某品某品名目,阿難所定。凡阿難記事之言,不得僭稱佛言。如云:佛說是《妙音菩薩來往品》時,阿難原文當作是妙音菩薩來往時;佛說是《普門品》時,阿難原文當雲是無盡意菩薩供養觀世音時;持地白佛言有人聞是《普門品》者,原文當作有人聞佛說觀世音功德者;以此例推,可一一臆改也。
第二十問:後經前經,意指分別。答:前經說跡,跡中有本;後經說本,本中有跡;無以易天台矣!跡猶他也,本猶自也。
第二十一問:使與前經銜尾相承,由跡生本可乎?答:不可。各自為經,多寶佛為證明壽量,出見於世可矣;如其銜尾,則是前說已說,後說未說,多寶隻證明前說,不證明後說,一不安也。則是下方海眾,隻擁護前說,不擁護後說,不安二。則是三周說法、三根授記,但為《如來壽量品》之序分,如此科判,不安三。設非因前言生後言,因前事生後事,則如來壽量,其終悶而不宣乎?正宗分是佛大事,不得因前事始生後事,不得因前言始生後言,如此科判,不安四。一經之中,乃各自為序、正、流通,斷無此例,不安五。不但文殊入海,脫文窒礙而已。
第二十二問:天台判本門跡門,截然兩大支,兀然相對峙,吾子之先聲也,以《下方湧出品》,為如來壽量之由序,以《見寶塔品》、《龍女獻珠品》還於前半,目為前半之流通,何害於義而不可哉?子殆欲與天台立異?答:《多寶佛品》是更端之相,非流通之相,不可還前半。何也?多寶佛是十一品主,是十一品脈,是十一品線,是十一品筋,是十一品眼,是十一品鑰匙,是十一品歸墟,我故與天台小異,《龍女品》文殊出海與前不屬,我故與天台小異。
第二十三問:後十一品之名《妙法蓮華經》,多寶佛所名,不可易矣。許有異名乎?答:亦得名為《平等大慧經》,亦得名為《釋迦壽量經》,亦得名為《多寶佛出見經》,亦得名為《多寶佛證明釋迦壽量經》。
第二十四問:佛於授舍利弗記之時,金口親宣,自名所說為妙法蓮華法,何也?答:妙法蓮華法,三世佛所說,曠劫預定,故釋迦三周說法之中,一字一句,皆自名為妙法蓮華法,此無可疑者。
第二十五問:十方三世所說《妙法蓮華經》可知者凡幾?答:見於《妙法蓮華經》稱引者凡五,與今經而七:一、日月燈明佛說,一、日月淨明德佛為一切眾生喜見菩薩說,一、提婆達多夙世所說,一、大通智勝如來說,一、威音王說,是為五,與今經而七也。
第二十六問:文殊入海所以教龍女者,當是何等《妙法蓮華經》?答:是釋迦牟尼佛在娑婆世界所說,即此前十品三周說法、三根授記、以《四安樂行》為流通者也。何用知之?曰:釋迦見主,文殊見輔。
第二十七問:如仁所說,震旦通行之經,訛闕、顛倒、蔓衍、複重如亂絲,已舉數事。更有明徵乎?答:《天台玄義》有之曰:他經皆說經題,此獨不說,非不說,其文未度也。(此一徵也。又此經為北朝宮女所亂,後來南嶽大師複理之,見《文句》此又一徵也。)
第二十八問:更有否?答:《普門品》偈:「偈答無盡意」五字,應入阿難語;應是爾時佛以偈答:「無盡意曰……」十字,不應誤入祗夜。譯者憒憒,一至於此,餘可例矣。
第二十九問:前經別行不連後,幹震旦有徵乎?答:有之。六祖大鑒大師《壇經》第七則曰:有人谘問《法華經》大義,祖命誦其文,誦至《化城喻品》,祖遽曰:止,即口授大義雲雲。六祖所言與天台智者大師之言,無二無別,謂之六祖所撰《法華玄義》可矣,謂之六祖所授《摩訶止觀》、六祖《法華三昧》無不可矣。夫六祖者,文殊化身也。
第三十問:以何因緣,二經俱至震旦?答:眾生因緣、根性、福力,各各不同,合而讀之,用證三昧,分而讀之,用證三昧,無不可者。他方世界種種國土所感,種種言詞,種種音聲,種種文字,或一句、或半偈,乃至一會,乃至如此間聞二會,乃至聞恒河沙數會,種種別異,必可知矣。
第三十一問:《見寶塔品》以爾時二字發端耶?答:必有如是我聞,必有序法會雲雲,必有當說《妙法蓮華經》雲雲,譯主欲衍尾,因刪之矣。餘可例知。
第三十二問:後經有多寶佛,猶前經之有文殊耶?答:如是。
第三十三問:文句間尚有纖疑存者乎?答:《提婆達多品》,前半記授記事,後半記龍女事,不相屬,疑二品誤合也,姑仍厥舊。
第三十四問:前三周簡矣,何以言初善、中善、後善?答:就三周而論,為上根說法,授上根記,初善也。為中根說法,授中根記,中善也。為下根說法,授下根記,後善也。就每周之中而論,初中後具在經文;就全經而論,《方便品》說一大事因緣,初善也。三周辟喻,中善也。文殊問四《安樂行》,說《髻珠喻》以終之,後善也。
第三十五問:流通屬累繁何傷乎?答:向不雲乎?有不說之說,有說之說,佛之本懷,視說之說不如不說之說之妙,說已贅矣,而說此至無意味之說豈妙耶?天台九旬譚妙,亦曾譚囑累妙、流通妙、自讚妙、校量罪福妙耶?
第三十六問:全經顛倒、重複、蔓衍之故。答:易知也!西土有諸講師,家置一編,戶抱一偈,名聞利養之故。造作文字,有經之臣仆,有經之輿佁,輿佁又有輿佁焉。假如西土人來譚《春秋》、《論語》,我土儒者,取《春秋》、《論語》付之,又誤取二書之注疏付之,又誤取二書之近世製舉文付之,又誤取製舉文之坊刻評論付之,西土人不別也,盡譯之以歸。《法華》二十八品之東,亦若是乎。
第三十七問:阿難記事倍於記言。佛言本簡,今又頗乙去佛讚,此經之文,佛言益簡。答:榛楛翦而栴檀出矣,礫石去而甄叔迦見矣。前經三周說法,後經說壽量,一切經所說統於是說,而重之以說妙音菩薩事,說常不輕事,說藥王事,說觀世音事,說妙莊嚴王事,以證明之。上根之者,但聞一事,疾得三昧,何苦簡乎?
第三十八問:嚐讀吾子《正譯》七篇矣,抑十不二門,大開圓解心,具三世法,固無所謂先後、延促、始終、來去者也。五十小劫禮佛,佛神力故,才如半日。據此,則凡形跡之不符,文氣之不承,教相之不同世相,文法之不同世傳記,願皆勿疑。答:凡此圓解,我皆具知,有理有事。稱理而論,無延促、先後、去來、終始,就事而論,則不然,佛不壞假名而說實相。種種示見,《如來壽量品》後半既自明之矣;當其示見佛,亦人也,亦一立言之大師也。阿難一載筆之史也,一代時教無此立言之相矣。釋迦諡為文,無此文章之體裁矣。非立言之相,非文章之體裁,非示見矣。
第三十九問:何以須論文義?答:報文佛恩故。
第四十問:日月燈明佛之經,提婆夙世說之經,藥王夙世聞之經,大通智勝如來之經,威音王之經,與今之二經,七者同乎不乎?答:非同非不同,亦同亦不同。劫不同,世界不同,佛身大小不同,佛壽延促不同;眾生有福無福根利鈍不同,經之字句多寡不同,說之之延促不同,此吾跡門也。心具十方、三世,法無多寡、延促,同且為贅詞,何況不同!以要言之,十方三世,我不見有一色一香非是《法華經》者,此吾本門也。今方與汝重定《法華》文句,科判其品,考核其文,甄中西之末流,補古師之千慮,就示見相而論其示見之始終本末,我寧論跡,我不暇與汝論本也。
第四十一問:願聞《法華玄義》。答:義學之淵海,三藏之總龜,法王之首輔,大士之化身,願盡劫皈依,為不侵不叛之臣。
第四十二問:子重定《法華》之文,悍如此,不問罪福乎?答:凡我所說,不合佛心,凡我所判,不合阿難原文,我為無知,我為妄作,違心所安,誑彼來學,我判此竟,七日命終,墜無間獄,我不悔也。如我所言,上合佛心,我所科判,上合阿難原文,佛加被我,智者大師加被我,我疾得《法華》三昧,亦得普見一切色身三昧,見生蒙佛夢中授記,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 時道光丁酉春正月,實《法華經》入震旦之一千四百四十四年。計定庵所刪七品,定為兩部,存者二十一品,又刪《藥王》半品。
重輯六妙門序
昔者大師判八教曰:藏、通、別、圓、頓、漸、秘密、不定。前四教之儀,後四教之相。自初禪、四禪、四無量心,展轉至於師子奮迅三昧,漸也;《摩訶止觀》、《覺意三昧》兩部,頓也。秘密,未說。《六妙門》、《十六特勝門》、《通明觀》三部,不定也。《六妙門》何以不定?曰:門門不定,因不定,果不定。一曰數,數者,三藏教五停心之一停心。但契經不雲乎?阿那波那,三世一切佛入道初門,此門徹下徹上,不局藏教。不定者一也。二曰隨,隨者,《十六特勝門》中之先鋒,因隨以知息出入相,冷暖澀滑,促長相,除身相,恃隨階神通特勝攝,不專取通妙門攝,隨之本旨異矣,隨以後次第又異。不定者二也。問:數隨二門,凡觀不淨,大不淨者,必先由之;故合不淨觀,謂之二甘露門,要是凡夫禪,小乘法。若夫圓人、四念處總十法界以為處,觀非淨非不淨;又觀息法,觀無常也;圓人則觀非常非無常;此為淺狹,彼為高遠。應之曰:汝論理,非論事,理則誠然。六祖門徒元策,遊河朔,遇禪人智隍,見其入定而笑之曰:定有入出耶?理亦誠然。我以事論,則大不然,不跏趺坐,則四威儀中,取何者為相?不停心,則雖有無上知見,為煩惱風,動搖慧燈,若存若滅,不知風相,那知地水火相?不知內四大相,那獲天眼通,見千世界相?常行常坐,半行半坐,古人克期為之,克期則有出入明矣。故有慧行,有行行,圓悟者側修,下學者上達。且夫妄心不異於真心者,豈指下手處言?妄之不揀,難用功故。聞訶栴檀,不得反取糞故。十五門禪,古德目初禪為根本禪,以用阿那波那故。《摩訶止觀》有二十五科,為前方便,方便中亦有調息一門,息如不調,心如猿猴,難可製故。三曰止,用製心止也。雖雲用製心止,不及三大止,但視乎其人爾。未開圓解,且用製心止,製心一處,何事不辦?如開佛知見矣,於跏趺時,用三種大止,用體真止,即空而假而中焉可矣;用隨緣方便止,即假而空而中焉可矣;用息二邊分別止,即中而空而假焉無不可矣;神明規矩,弘道者人。不定者三也。四曰觀,此部之觀,先觀息,乃觀身受心法四倒,成四念處,其觀息也略;但四念處之喤引而已。特勝通明,由觀息克取神通,故詳;此門或取通,或不取通,故略。及其成四念處也,是四枯四念處,非四榮四念處,為未圓人聊說如此。圓人三種大觀,不縱不橫,全體大用,正在此時,借在此時,無不可矣。不定者四也。五曰還,此門還是裂小網,開佛知見曰裂大網,還者非他,《覺意三昧》之觀,觀心是也,夫亦各還其所還而已矣。不定者五也。六曰淨,準上此淨,但是聲聞淨,聲聞析假入空得稱淨,緣覺體假入空亦稱淨;乃知如來四德,亦受淨名。不定者六也。有至定者存乎?曰:名目定,網格定,次第不可紊則定,首尾相注則定。元藏目錄《六妙門》三卷,在「謹」字函,為大師全書二十七種之一。明藏南北皆闕,惜哉,痛哉!讀《釋禪波羅密次第門》十卷,其第七卷曰:《六妙門》才二千言,非元藏單行本。元藏既不可見,此亦足以窺全指於十四乎?未可知也。刻木行,以少慰天台裔人求古笈之誌,微此,不定一門熄矣。大清道光十八年仲冬朔日觀實相之者滌筆敘。
支那古德遺書序
觀實相之者愾然曰:學術有升降,人心有誠偽,水有淄、澠,樂有《雅》、《鄭》,豈獨九流之通蔽,儒門之口實而已乎?原夫禪者,佛說六波羅密門之一門,古所謂禪,盡事禪也。千佛所胎息,三乘所劬勞,八教所管鑰,盡事禪也。入之也有門,踐之也有途,譬彼登山,足無藉則何以為之階?手無捫則何以為之援?而且導之也有師,扶持之也有相,尚猶慮夫涉之也有淺深,閱之也有久暫,則有諸境以為之策,有化城以為之止息,乃有大事因緣以為之歸墟。其言明且清也,故被乎三根,其術至樸實平正也,故其書三根學焉而各無弊,莊論法語,尚懼不聰,烏有所謂機鋒者乎?名身句身,尚懼不明,烏有所謂參悟者乎?是非有檢束,烏有所謂一千七百則公案乎?通塞視前途,烏有所謂看話頭者乎?慈和暖愛,烏有所謂棒喝者乎?有聞、有思、有修,以言說說其無言說,以思議思議其不思議,必有悉檀焉,烏有一切镵者乎?傾肝吐鬲而予之,烏有設伏以俟敵者乎?蓋惟恐人之不好問也,烏有來即攔,到即斫者乎?無量人問,當用無量法門悉檀答之,譬如醫門四百四病,四百四藥,診脈處方,臨時區配,烏有以現成語句,囫圇籠罩人者乎?或宗《華嚴經》,或宗《法華經》,或宗《涅槃經》,荊溪讚天台云:「依經帖釋,理富義順。」烏有所謂教外別傳者乎?或難之曰:天台所雲雲,都在《法華》七卷內耶?應之曰:書不盡言,言不盡意,作者無之,述者有之,九流之通例如此矣。智者大師即補結集者之略,又正翻譯者之拙,又或囊括大意,或融合眾文,或發揮孤文,或不忽旁沈,或搜剔隙罅,或舉一例諸,微獨禪人而已。支那賢者讀周公、孔父之書,皆如此矣,烏有所謂教外之別傳者乎?如青天白日,欲人之無不見也,烏有所謂祖師向上事,密密不通風者乎?幽探冥討,旁引殽證,尚懼靈文之不富也,烏有撥去語言文字者乎?其書不幸而埋藏,千載無者宜也,其書幸而流布,得道者如麻、如菽、如竹葦又宜也,烏有所謂孤提祖印,密付衣缽者乎?以佛為師,以佛知見為歸,以經論為導,以禪為行,烏有所謂不向如來行處行者乎?悲夫!晚唐以還,像法漸謝,則有斥經論用曹溪者,則有祖曹溪並失夫曹溪之解行者,愈降愈濫,愈誕愈易,昧禪之行,冒禪之名,儒流文士,樂其簡便,不識字髡徒,習其狂猾,語錄繁興,夥於小說,工者用廋,拙者用謠,下者雜俳優成之,異乎聞於文佛之所聞,狂師召伶俐市兒,用現成言句授之,勿失腔節,三日,禪師其遍市矣。佛言:吾如師子王,不畏百獸,畏師子身自生蛆蟲,啖師子肉。佛法之衰,為支那所詆,不絕如線,則豈非蛆蟲僧之召之也哉?予疚焉!又焉!亟思所以報佛恩者,乃寫《法華》宗魏南嶽思大師書一種四卷,隋天台智者大師書若干種若干卷,唐荊溪湛然大師書若干種若干卷,《涅槃》宗唐永嘉無相大師書一種一卷,《華嚴》宗唐帝心大師書一種一卷,圭峰密大師書一種二卷,書其地曰支那,尊其人曰古德,目其教,信其必不離語言文字也,故謂之遺書。既寫定,藏之乎羽岑之山,支那緇白,容有續九流諟古今審正變者焉。以二百本施諸寺。
最錄三千有門頌
《三千有門頌》,三十六句,二百五十六字,宋陳瓘瑩中撰。明僧百鬆解;附瑩中與南湖講師書一篇,合一卷。其曰《有門頌》,書中目詳之矣,不贅論。自珍始讀天台性具宗,駭而仇之,何也?佛具佛性,我知之,九界具佛性,我知之,九界具九界性,我知之,佛具九界性,獨未之聞。嚐欲改百界為九十一界,改千如為九百十如,改三千門為二千七百三十門。壬辰歲,得此書於龍泉寺,思之七晝夜,乃砉然破!駭者成粥飯,仇者成骨肉,移之念佛三昧立證。三昧雲何?曰:以彌陀性具法界中之我,念我性具法界中之彌陀,非三昧乎?乃莊寫最錄之如此。最錄竟,誦《法華偈》曰:「是法住法位,世間相常住。」
最錄禪波羅蜜門
禪有三翻:定也,思惟修也,功德林也,此六波羅蜜之第五門。經言非禪不智;又言無定之慧,如風中燈,照物不了故,此波羅蜜猶密室燈也。書分四分,未說一分,說三分,三分共十五門。十五門之修行下手處,分三門,曰觀息,曰觀身,曰觀心。觀必以止為門,故此書亦得稱止觀,乃南嶽所授三種《止觀》之一也。止為前方便,觀是正宗分,觀息謂之阿那波那門也。觀身即不淨觀、大不淨觀也,此二者,謂之二種無上甘露門。全書十卷,菁華不外此二義,有所觀淺深不同,層累盤旋,如鳥道而漸上,以為詮次耳。觀息與身詳,觀心略,惟通明觀中,近似觀心論耳。著書各體裁,不以觀心為主,欲知觀心三千具,觀心即假即空即中,有《摩訶止觀》百軌則在,至此書歸墟,在乎神通,觀息亦得通,觀身亦得通,實乃修通之大宗也。無記化化禪,則有妙玄在。原錄云:「大師於瓦棺寺說《大莊嚴寺法慎私記》,凡三十卷,章安頂禪師治定為十卷,八九十略,無七修證中四別,惟至第三出世,但至對詒云,大師嘗在高坐曰:『若說次第禪門,年可一遍,若著章疏,可五十卷。』今刊頂示大科云云。」序判並精細明白,不知何人所為?在北藏「煩」字函。丁酉九月記。
最錄八識規矩頌
《八識規矩頌》唐玄奘師撰。自天親造三十頌,《護法》等十菩薩各敷演之,各為十卷。師受窺基之請,合百卷之書,刪其義之不可立者,與義之不並立者為十卷。則今藏本《成唯識論》是,學者睹慈恩宗如日在天矣。師複念言法相宗大綱在八識,大緯在四分,乃製此頌一十二章,分四大支,初三頌眼等識,次三頌意識,次三末那,次三賴耶。每支各攝證自證分、自證分、相分、見分等。又每支前三章頌凡也,後一章頌聖也,昔世尊說經,必重宣厥義而說偈言,此亦大師說唯識竟,重宣說偈者也。又其名身句身,與天親之頌相似,將毋天親示見者哉?
最錄七佛偈
《七佛偈》總一百八十八言,元虎溪師疑其偽。龔自珍曰:《七佛偈》無可疑也。凡虎溪所疑,及踵虎溪而疑者,總有四義,作九重破之:第一疑,謂大藏中無單行,故疑。破曰:教外別傳,不在阿難結集中,破之一。複次,三藏十二部,各有體裁,伽陀隻夜皆不單行,此伽陀也,前後無附麗牽連之文,不得單行,破之二。複次,達摩西來;口述梵語,未入大藏,破之三。第二疑,謂無譯主之名,故疑。破曰:西土無齎來之貝氎,此土無詔譯之帝王,譯主輩馮何見之,而馮何譯之?破之四。複次,達摩口傳,即是達摩所譯,譯主許譯經,達摩何以不許譯偈?破之五。第三疑,謂天台慈恩賢首三家。皆不引其文,故疑。破曰:達摩口傳至於六祖,六祖《壇經》數佛,必數釋迦以前之六佛,《壇經》豈亦不可信乎?破之六。支那撰述引之者,有永明壽師《宗鏡錄》、《景德傳燈錄》、契嵩大師《鐔津集》,皆北宋以前矣,何必天台賢首?至慈恩宗,本不譚此義,宜其不引也。破之七。複次,六祖《壇經》不引之引,何子明引其文首尾具,始為引乎?破之八。第四疑,謂《付法藏因緣傳》無之,故疑。破曰:著書者各有托始,此傳托始釋迦,有何可疑?破之九。以上九重義破四重疑竟。問:有舛文乎?答:《拘留孫偈》,第二句第七字是了字,非幻字,作幻字則蔓矣。《宗鏡錄》不誤。近世獨鼓山刻《禪海十珍集》不誤,天下叢林處處誤。
最錄達摩大師說四行
達摩《說四行》一卷,僧璨之所傳也。一、報冤門,無怨忿行;二、隨緣門,無忻喜行;三、無求門,無所求行;四、波羅蜜門,不取相行。自珍曰:自祖之東,指人心,遮語言文字,此雖語言哉,懇乎愨,齊乎樸,衝乎寥乎其易知。自珍又曰:似四十二章經。
最錄壇經
記者冗不殺,故精英奄然,示宋景德以來所錄,此最樸直,最雅馴矣。祖所獲於《法華》、《涅槃》也,與吾智者大師同,謂之六祖撰《法華玄義》可,謂之《涅槃玄義》可,謂之六祖《摩訶止觀》,無不可矣。其斥淨土也,開唯心之宗,最上法門,我實不見其謗淨土。五燈以還,險語過此者多有,何獨議六祖?嗚呼!如六祖,我敢謂禪不可捕捉也哉!
最錄大乘止觀
魏南嶽慧思大師《大乘止觀》四卷。龔自珍曰:此龍樹涅槃後,第一出世法王子也,故天台標三止,此先標止;天台標三觀,此先標觀;天台以止為觀,以觀為止,此先標止觀雙行。天台說性具,一念十法界,此性具宗之始。天台云:八識中第六功能大,此用意識之始。天台十重軌則,此六重括十重也。此書唐時亡,慈雲大師知白購之海舶中,仍魏世本,明藕益大師智旭注之,國朝單居士炤刻之,支那撰述無更古於是者,稱說讚歎,如贅疣然。所能言者,盡於此矣。
最錄覺意三昧
或問之曰:天台智者大師舍八而用六何也?答曰:舍六無可用也,天台之功,斯為最大。今夫八識眾生,不自知其有;不知其有,而欲用力以厄之也末由。六識眾生,自知其有,自知其有,則可以厄其四運,用其雙照,以入乎中道。語曰:「一夫當關,萬夫莫開。」天台之功,斯為最大。先說《四念處》,後說《覺意三昧》,皆說三十七道品也。徑山刻本有《四念處》,無《覺意三昧》,予故表微。梵本六卷,假之龍泉寺。
最錄四念處
《四念處》四卷,隋天台山智者大師之所說,門人灌頂大師之所筆受;明吳江吳士龍從藏本刻者。《四念處》者,三十七助道品之四也。天台判四教,第一卷說藏教五停心四念處,第二卷說通教五停心四念處,第三卷說別教五停心四念處,第四卷說圓教五停心四念處。五停,緯也;四念,經也。藏、通、別,客義也,圓,主人義也。提綱用四義攝,曰:生生四念處,生不生四念處,不生生四念處,不生不生四念處。何所祖?祖龍樹中論也。天台如日出,龍樹其啟明也。推之七菩提分,八聖道分,亦必各具四教儀,惜不可聞矣。
卷八己卯
吳山人文徵、沈書記錫東餞之虎邱
一天幽怨欲誰諳?
詞客如雲氣正酣。
我有簫心吹不得,
落花風裏別江南。
〈──《定庵集外未刻詩》〉
題吳南薌東方三大圖
〈圖為登州蓬萊閣,為泰州山,為曲阜聖陵。〉
禽父始宅奄,猶未荒大東;
周王有名祀,名山止龜蒙;
尚父賜履海,泱泱表大風;
時無神仙言,不睹金銀宮。
春秋貶宋父,坐失玉與弓;
祊田富湯沐,季旅何懜懜?
秦穆作西畤,帝醉終可逢;
恒無三脊茅,遂輟登山蹤。
頑哉魯與齊,靈氣不牖衷,
孤負介海岱,海深岱徒崇。
素王張三世,元始而麟終;
文成號數萬,太平告成功;
其文富滄海,其旨高蒼穹。
於是海岱英,盡入孔牢籠。
熙朝翠華至,九跪迎上公;
厥典盛謁林,漢後無茲隆。
惜哉有闕遺,未舉金泥封;
小臣若上議,廷臣三日聾。
首謁孔林畢,繼請行升中;
繼請射滄海,三事碑三通。
古體日霾晦,但嗤秦漢雄;
周情與孔思,執筆思忡忡。
〈──《定庵集外未刻詩》〉
行路易
東山猛虎不吃人,西山猛虎吃人;
南山猛虎吃人,北山猛虎不食人。
漫漫趨避何所已?
玉帝不遣牖下死,一雙瞳神射秋水。
袖中芳草豈不香?
手中玉麈豈不長?
中婦豈不姝?
座客豈不都?
江大水深多江魚,江邊何嘵呶?
人不足,盱有餘,夏父以來目矍矍。
我欲食江魚,江水澀嚨喉,魚骨亦不可以餐;
冤屈復冤屈,果然龍蛇蟠我喉舌間,
使我說天九難、說地九難、踉蹌入中門。
中門一步一荊棘,大藥不療膏肓頑,
鼻涕一尺何其孱?臣請逝矣逝勿還。
嘈嘈舟師,三五詈汝:
汝以白晝放歌為可惜,而乃脂汝轄;
汝以黃金散盡為復來,而乃鞭其脢。
紅玫瑰,青鏡台,美人別汝光徘徊。
腷腷膊膊,雞鳴狗鳴;
淅淅索索,風聲雨聲;
浩浩蕩蕩,仙都玉京。
蟠桃之花萬丈明,淮南之犬彳亍行;
臣豈不如武皇階下東方生?
亂曰:
三寸舌,一枝筆,
萬言書,萬人敵,九天九淵少顏色;
朝衣東市甘如飴,玉體須為美人惜。
〈──《定庵集外未刻詩》〉
夢得
〈夢得「東海潮來月怒明」之句,醒,足成一詩。〉
曇誓天人度有情,上元旌節過雙成。
西池酒罷龍嬌語,東海潮來月怒明。
梵史竣編增楮壽,花神宣敕赦詞精。
不知半夜歸環佩,問是空峒第幾聲。
〈──《定庵集外未刻詩》〉
又成一詩
東海潮來月上弦,空峒撫罷靜諸天。
西池一宴無消息,替管桃花五百年。
〈──《定庵集外未刻詩》〉
鄰兒半夜哭
鄰兒半夜哭,或言憶前生;
前生何所憶?或者變文名。
我有一篋書,屬草殊未成,
塗乙迨一紀,甘苦萬千並!
百憂消中夜,何如坐經營?
翦燭蹶然起,婢笑妻復嗔;
萬一明朝死,墮地淚縱橫。
〈──《定庵集外未刻詩》〉
雜詩
〈己卯自春徂夏,在京師作,得十有四首。〉
少小無端愛令名,也無學術誤蒼生。
白雲一笑懶如此,忽遇天風吹便行。
文格漸卑庸福近,不知庸福究何如?
常州莊四能憐我,勸我狂刪乙丙書。
情多處處有悲歡,何必滄桑始浩歎!
昨過城西曬書地,蠹魚無數訊平安。
手種江山千樹花,今年負殺武陵霞。
夢中自怯才情減,醒又纏綿感歲華。
龐眉名與段公齊,一脈東原高第題。
回首外家書帙散,大儒門祚古難躋。
昨日相逢劉禮部,高言大句快無加;
從君燒盡蟲魚學,甘作東京賣餅家。
十年提倡受恩身,慘綠年華記憶真。
江左名場前輩在,敢將名氏廁陳人。
偶賦山川行路難,浮名十載避詩壇。
貴人相訊勞相護,莫作人間清議看。
萬柳堂前一柳無,詞流散盡散樵蘇。
山東不少升平相,為溯前茅馮益都。
荷葉粘天玉蝀橋,萬重金碧影如潮;
功成倘賜移家住,何必湖山理故簫。
交臂神峰未一登,夢吞丹篆亦何曾?
丈夫三十愧前輩,識字遊山兩不能。
樓閣參差未上燈,菰蘆深處有人行。
憑君且莫登高望,忽忽中原暮靄生。
東抹西塗迫半生,中年何故避聲名?
才流百輩無餐飯,忽動慈悲不與爭。
欲為平易近人詩,下筆清深不自持。
洗盡狂名消盡想,本無一字是吾師。
〈──《定庵集外未刻詩》〉
題紅蕙花詩冊尾(並序)
〈蘇州袁廷檮,字又凱,有王晉卿、顧仲瑛之遺風,文酒聲伎,江南北罕儷者。當時座客,極東南選,而家大人未第時,亦曾過其宅。君死後,家資泯然。今年冬,有絺而秀者,來謁於蘇鬆太道官署,寒甚,出晉硯求易錢,則又凱嗣君也,大人贈以資,不受其硯。噫!西華葛帔,劉竣著書,所從來久矣。鈕非石亦其座上客,非石嘗為君致洞庭山紅蕙花一本,君大喜,貯以汝州瓷,繪以宣州紙,顏其室曰:紅蕙花齋;名其詩文曰:《紅蕙齋集》;刻其管曰:紅蕙齋筆;又自製《紅蕙花樂府》,付梨園部;又徵人賦紅蕙詩,海內詞流,吟詠殆遍。今嗣君抱來烏絲闌素冊高尺許,皆將來蕙故也。君之風致可想見矣。餘悲盛事不傳,感而題於冊尾。〉
香滿吟箋酒滿卮,楓橋賓客夜燈時。
故家池館今何許?紅蕙花開空染枝。
讀罷一時才子句,《騷》香漢豔各精神。
十年我恨生差晚,不見風流種蕙人。
歌板無聊舞袖涼,江南詞話斷人腸。
人生合種閑花草,莫遣黃金怨國香。
眼前誰是此花身?寂寞猩紅萬古春。
花有家鄉儂替管,五湖添個泛舟人。
〈──《定庵集外未刻詩》〉
張詩舲前輩遊西山歸索贈
鸞吟鳳叫下人寰,絕頂題名振筆還。
樵客忽傳仙墨滿,禁中才子昨遊山。
去年扈從東巡守,玉佩瓊琚大放辭。
等是才華不巉削,願攜康樂誦君詩。
畿輔千山互長雄,太行一臂怒趨東。
祝君腰腳長如意,吟遍蜿蜒北榦龍。
〈──《定庵集外未刻詩》〉
庚辰
驛鼓三首
河燈驛鼓滿天霜,小夢溫黁亂客腸。
夜久羅幬梅弄影,春寒銀銚藥生香。
慈闈病減書頻寄,稚子功閑日漸長。
欲取離愁暫拋卻,奈君針線在衣裳。
釵滿高樓燈滿城,風花未免態縱橫。
長途借此銷英氣,側調安能犯正聲?
綠鬢人嗤愁太早,黃金客怒散無名。
吾生萬事勞心意,嫁得狂奴孽已成。
書來懇款見君賢,我欲收狂漸向禪。
早被家常磨慧骨,莫因心病損華年。
花看天上祈庸福,月墮懷中聽幻緣。
一卷金經香一炷,懺君自懺法無邊。
〈──《定庵集外未刻詩》〉
發洞庭
〈舟中懷鈕非石樹玉、葉青原昶。〉
西山春晝別,兩袖落梅風。
不見小龍渚,尚聞隔渚鍾。
樽前荇葉白,舵尾茶華紅。
仙境杳然杳,酸吟雨一篷。
〈──《定庵集外未刻詩》〉
此遊
此遊好補前遊罅,揮手雲聲浩不聞。
兩度山靈濡筆記,錢塘君訪洞庭君。
舟到西山岸,尋幽迤邐斜。
居然六七里,無境不煙霞。
遂發石公寺,定過神女家;
雲和風靜裏,已度萬梅花。
風意中流引,香煙在嶼遲。
悠揚聞杜若,仿佛邀蛾眉。
白日憺明鏡,春空飄彩旗。
湖東一回首,萬古長相思。
〈──《定庵集外未刻詩》〉
過揚州
春燈如雪浸蘭舟,不載江南半點愁。
誰信尋春此狂客,一茶一偈過揚州。
〈──《定庵集外未刻詩》〉
觀心
結習真難盡,觀心屏見聞。
燒香僧出定,嘩夢鬼論文。
幽緒不可食,新詩如亂云。
魯陽戈縱挽,萬慮亦紛紛。
〈──《定庵集外未刻詩》〉
又懺心一首
佛言劫火遇皆銷,何物千年怒若潮?
經濟文章磨白晝,幽光狂慧復中宵。
來何洶湧須揮劍,去尚纏綿可付簫。
心藥心靈總心病,寓言決欲就燈燒。
〈──《定庵集外未刻詩》〉
庚辰春日重過門樓胡同故宅
城西郎官屯,多官閱一宅。
家公昔為郎,有此湫隘室。
朝陽與夕陽,屋角紅不積;
春雨復秋雨,雙扉故釘齒。
無形不知老,有質乃易蝕;
往事思之悔,至理悟獨立。
中有故我魂,三呼如欲出。
〈──《定庵集外未刻詩》〉
因憶兩首
因憶橫街宅,槐花五丈青。
文章酸辣早,《知覺》鬼神靈。
大撓支干始,中年記憶熒。
東牆涼月下,何客又橫經。
因憶斜街宅,情苗茁一絲。
銀缸吟小別,書本畫相思。
亦具看花眼,難忘授《選》時。
泥牛入滄海,執筆向空追。
〈──《定庵集外未刻詩》〉
客春
〈住京師之丞相胡同,有《丞相胡同春夢詩》二十絕句。春又深矣,因燒此作,而奠以一絕句。〉
春夢撩天筆一枝,夢中傷骨醒難支。
今年燒夢先燒筆,檢點青天白晝詩。
〈──《定庵集外未刻詩》〉
春晚送客
潞水滔滔南向流,家書重疊附征郵。
行人臨發長亭晚,更折梨花寄暮愁。
〈──《定庵集外未刻詩》〉
琴歌
之美一人,樂亦過人,哀亦過人。
月生於堂,匪月之精光,睇視之光。
美人沈沈,山川滿心。
落月逝矣,如之何勿思矣?
美人沈沈,山川滿心。
吁嗟幽離,無人可思。
〈──《定庵集外未刻詩》〉
偶感
昆山寂寂弇山寒,玉佩瓊琚過眼看。
一事飛騰羨前輩,升平時世讀書官。
〈──《定庵集外未刻詩》〉
趙晉齋魏、顧千里廣圻、鈕非石樹玉、吳南薌文徵、江鐵君沅,同集虎邱秋宴作
盡道相逢日苦短,山南山北秋方腴。
兒童敢笑詩名賤,元氣終須老輩扶。
四海典彝既旁達,兩山金石誰先儲。
影形各各照秋水,渣滓全空一世無。
〈──《定庵集外未刻詩》〉
題虎跑寺
南山蹕路丙申開,庚子詩碑鎖綠苔。
曾是純皇親幸地,野僧還盼大行來。
〈──《定庵集外未刻詩》〉
杭州龍井寺
紅泥亭倒客來稀,鐘磬沉沉出翠微。
無分安禪翻破戒,盜他常住一花歸。
〈──《定庵集外未刻詩》〉
懷沈五錫東、莊四綬甲
白日西傾共九州,東南詞客愀然愁。
沈生飄蕩莊生廢,笑比陳王喪應、劉。
〈──《定庵集外未刻詩》〉
鳴鳴硻硻
黃犢怒求乳,樸誠心無猜;
犢也爾何知,既壯恃其孩。
古之子弄父兵者,喋血市上寧非哀?
亦有小心人,天命終難奪;
授命何其恭?履霜何其潔?
孝子忠臣一傳成,千秋君父名先裂。
不然冥冥鴻,無家在中路;
恝哉心無瑕,千古孤飛去。
嗚嗚復嗚嗚,古人誰智誰當愚?
雰復雰,智亦未足重,愚亦未可輕。
鄙夫較量愚智間,何如一意求精誠?
仁者不訹愚癡之萬死,勇者不貪智慧之一生。
寄言後世艱難子,白日青天奮壁行。
〈──《定庵集外未刻詩》〉
幽人
幽人媚清曉,落月澹林光。
欲采蘅蘭去,春空風露香。
阿誰叫橫玉?驚起綠煙床。
亦有梅花夢,頹鬟待太陽。
〈──《定庵集外未刻詩》〉
和歸佩珊夫人贈詩
〈寒夜讀歸佩珊夫人贈詩,有「刪除藎篋閑詩料,湔洗春衫舊淚痕」之語,憮然和之。〉
風情減後閉閑門,襟尚餘香袖尚溫。
魔女不知侵戒體,天花容易隕靈根。
蘼蕪徑老春無縫,薏苡讒成淚有痕。
多謝詩仙頻問訊,中年百事畏重論。
〈──《定庵集外未刻詩》〉
昨夜
昨夜江潮平未平,篷窗有客感三生。
藥爐臥聽渾如沸,不似牆東釵釧聲。
種花都是種愁根,沒個花枝又斷魂。
新學甚深微妙法,看花看影不留痕。
〈──《定庵集外未刻詩》〉
紫雲回三疊(有序)
〈宋於庭妹之夫曰繆中翰,分校禮部試,於庭以回避不預試。予按樂府有《紫雲回》之曲,其詞不傳,戲補之,送於庭出都。〉
安香舞罷杜蘭催,水瑟冰敖各費才。
別有傷心聽不得,珠簾一曲《紫雲回》。
神仙眷屬幾生修,小妹承恩阿姊愁。
宮扇已遮簾已下,癡心還佇殿東頭。
上清丹籙姓名訛,好夢留仙夜夜多。
爭似芳魂驚覺早,天雞不曙渡銀河。
〈──《定庵集外未刻詩》〉
詠史
宣室今年起故侯,銜兼中外轄黃流。
金鑾午夜聞乾惕,銀漢千尋瀉豫州。
猿鶴驚心悲皓月,魚龍得意舞高秋。
雲梯關外茫茫路,一夜吟魂萬里愁。
一樣蒼生係廟廊,南風愁絕北風狂。
羽書顛倒司農印,幕府縱橫急就章。
奇計定無賓客獻,冤氛可顧子孫殃?
何年秘客搜詩史,輸與山東客話長。
〈──《定庵集外未刻詩》〉
逆旅題壁,次周伯恬原韻
名場閱曆莽無涯,心史縱橫自一家。
秋氣不驚堂內燕,夕陽還戀路旁鴉。
東鄰嫠老難為妾,古木根深不似花。
何日冥鴻蹤跡遂,美人經卷葬年華。
〈──《定庵集外未刻詩》〉
贈伯恬
毗陵十客獻清文,五百狻猊屢送君。
從此周郎閉門臥,落花三月斷知聞。
〈──《定庵集外未刻詩》〉
廣陵舟中為伯恬書扇
紅豆生苗春水波,齊梁人老奈愁何!
逢君衹合千場醉,莫恨今生去日多。
〈──《定庵集外未刻詩》〉
讀《公孫弘傳》
三策天人禮數殊,公孫相業果何如?
可憐秋雨文園客,身是貲郎有諫書。
〈──《定庵集外未刻詩》〉
馬
八極曾陪穆滿遊,白雲往事使人愁。
最憐汗血名成後,老踞殘芻立仗頭。
〈──《定庵集外未刻詩》〉
題崇禎戊辰科《題名錄》尾
〈吳市得題名錄一冊,乃明崇禎戊辰科物也,題其尾一律。〉
天心將改禮闈徵,養士猶傳十四陵。
板蕩人材科目重,蓁蕪文體史家憑。
朱衣點過無光氣,淡墨堆中有廢興。
資格未高滄海換,半為義士半為僧。
〈──《定庵集外未刻詩》〉
集漢瓦拓本字成詩
〈以漢瓦琢為硯賜橙兒,因集齋中漢瓦拓本字成一詩,並付之。〉
平生自□,傳世千秋,高官上第,甘與阿侯。
〈──《定庵集外未刻詩》〉
才盡
才盡不吟詩,非關象喙危。
青山有隱處,白日無還期。
病骨時流恕,春愁古佛知。
觀河吾見在,莫畏鏡中絲。
〈──《定庵集外未刻詩》〉
答鐵君
〈鐵君惠書,有「玉想瓊思」之語,衍成一詩答之。〉
我昨青鸞背上行,美人規勸聽分明;
不須文字傳言語,玉想瓊思過一生。
〈──《定庵集外未刻詩》〉
戒詩五首
蚤年攖心疾,詩境無人知。
幽想雜奇悟,靈香何鬱伊?
忽然適康莊,吟此天日光。
五嶽走驕鬼,萬馬朝龍王。
不遇善知識,安知因地孽?
戒詩當有詩,如偈亦如喝。
百髒發酸淚,夜湧如原泉。
此淚何所從?萬一詩祟焉。
今誓空爾心,心滅淚亦滅。
有未滅者存,何用更留跡?
行年二十九,電光豈遽收?
觀河生百喟,何如泛虛舟?
當喜我必喜,當憂我輒憂。
盡此一報形,世法隨沈浮。
天龍為我喜,波旬為我愁。
波旬爾勿愁,咒汝械汝頭。
律居三藏一,天龍所護持。
我今戒為詩,戒律亦如之。
墮落有時有,三塗報則否。
舌廣而音宏,天女侍前後。
遍召忠孝魂,座下賜卮酒。
屈曲繚戾情,千義聽吾剖。
卷九庚午
桂殿秋
〈六月九日,夜夢至一區,雲廊木秀,水殿荷香,風煙鬱深,金碧嵯麗。時也方夜,月光吞吐,在百步外,蕩瀣氣之空蒙,都為一碧,散清景而離合,不知幾重?一人告予:此光明殿也。醒而憶之,為賦兩解。〉
明月外,淨紅塵,蓬萊幽窅四無鄰。
九霄一派銀河水,流過紅牆不見人。
驚覺後,月華濃,天風已度五更鐘。
此生欲問光明殿,知隔朱扃幾萬重?
──《無著詞》
辛未
水調歌頭 (寄徐二義尊大梁)
去日一以駛,來日故應難。故人天末不見,使我思華年。結客五陵英少,脫手黃金一笑,霹靂應弓弦。意氣渺非昔,行役亦云艱。
湖海事,感塵夢,變朱顏。空留一劍知己,夜夜鐵花寒。更說風流小宋,淒絕白楊荒草,誰哭墓門田?遊侶半生死,想見涕潺湲。
又
〈辛未六月二日,風雨竟晝,檢視敗簏中嚴江宋先生遺墨,滿眼淒然,賦此解。〉
風雨颯然至,竟日作清寒。我思芳草不見,忽忽感華年。〈(謂嚴江宋先生。)〉憶昔追隨日久,鎮把心魂相守,燈火四更天。高唱夜烏起,當作古人看。
一枝榻,一爐茗,宛當前。幾聲草草休送,萬古遂茫然。仙字饑不食,故紙蠅鑽不出,陳跡太辛酸。一掬大招淚,灑向暮雲間。
──《懷人館詞》
點絳唇 (十月二日馬上作)
一帽紅塵,行來韋杜人家北。滿城風色,漠漠樓臺隔。目送飛鴻,影入長天滅。關山絕,亂雲千疊,江北江南雪。
──《懷人館詞》
瑤臺第一層
〈某侍衛出所撰《王孫傳》見示,愛其頗有漢晉人小說風味,屬予為之引,因填一詞括之,戲侑稗家之言。〉
無分同生偏共死,天長恨較長。風災不到,月明難曉,曇誓天旁。偶然淪謫處,感俊語小玉聰狂。人間世,便居然願作,長命鴛鴦。
幽香,蘭言半枕,歡期抵過八千場。今生已矣,玉釵鬟卸,翠釧肌涼。賴紅巾入夢,夢裏說別有仙鄉。渺何方?向瓊樓翠宇,萬古攜將。
──《懷人館詞》
鵲橋仙
〈同袁蘭村、汪宜伯小憩僧寺,宜伯製《金縷曲》見示,有「望南天、倚門人老,敢雲披」之句。余驚其心之多感,而又喜其詞之正也,倚此慰之。〉
飄零也定,清狂也定,莫是前生計左。才人老去例逃禪,問割到慈恩真個?
吟詩也要,從軍也要,何處宗風香火?少年三五等閑看,算誰更驚心似我?
──《懷人館詞》
浪淘沙 (有寄)
別夢醒天涯,怊悵年華。懷人無奈碧雲遮。我自低迷思錦瑟,誰怨琵琶?
小字記休差,年紀些些。蘇州花月是兒家。紫杜紅蘭閑掐遍,何處蘋花?
──《懷人館詞》
壬申
唐多令 (道中書懷)
二十五長亭,垂楊照眼青。付春風短夢零星。斜倚雕鞍無氣力,渾不似,俊遊人。
春意太憨生,春愁喚不醒。負華年誰更憐卿?惟有填詞情思好,無恙也,此花身。
──《懷人館詞》
浪淘沙 (舟中夜起)
幽夢四更醒,欸乃聲停。吳天月落半江陰。驀地橫吹三孔笛,聘取湘靈。
螺髻鎖娉婷,煙霧青青。看他潮長又潮平。香草美人吟未了,防有蛟聽。
──《懷人館詞》
高陽臺
南國傷讒,西洲怨別,淚痕淹透重衾。一笛飛來,關山何處秋聲?秋花繞賬瞢騰臥,醒來時芳訊微聞。費猜尋,乍道蘭奴,氣息氛氳。
多愁公子新來瘦,也何曾狂醉,絕不閑吟。璧月三圓,江南消息沈沈。魂消心死都無法,有何人來慰登臨?勸西風,將就些些,莫便秋深。
──《懷人館詞》
行香子 (道中書懷。與汪宜伯)
跨上征鞍,紅豆拋殘,有何人來問春寒?昨宵夢裏,猶在長安。在鳳城西,垂楊畔,落花間。
紅樓隔霧,珠簾卷月,負歡場詞筆闌珊。別來幾日,且勸加餐。恐萬言書,千金劍,一身難。
〈初相見,蒙填詞見詒,有「萬言奏賦,千金結客」二語。〉
附:送龔瑟人出都調水龍吟(汪琨宜伯)
長安舊雨都非,新歡奈又搖鞭去。城隅一角,明箋一束,幾番小聚。說劍情豪,評花思倦,前塵夢絮。縱閑愁鬥蟻,羈魂幻蝶,尋不到,江南路。
從此齋鐘衙鼓,料難忘,分襟情緒。瓜期漸近,萍蹤漸遠,合並何處?易水盟蘭,豐台贈芍,離懷觸忤。任紅蕉題就,翠筠書遍,餞詞人句。
──《懷人館詞》
醉太平 (道中作)
鞍停轡停,雲行樹行。東風昨夜吹魂,過青山萬痕。
春濃夢沈,愁多酒醒。一天飛絮愔愔,攪離懷碎生。
[1]
──《懷人館詞》
鵲踏枝 (過人家廢園作)
漠漠春蕪蕪不住。藤刺牽衣,礙卻行人路。偏是無情偏解舞,蒙蒙撲面皆飛絮。
繡院深沈誰是主?一朵孤花,牆角明如許!莫怨無人來折取,花開不合陽春暮。
──《懷人館詞》
湘月 (壬申夏,泛舟西湖,述懷有賦,時予別杭州蓋十年矣)
天風吹我,墮湖山一角,果然清麗。
曾是東華生小客,回首蒼茫無際。
屠狗功名,雕龍文卷,豈是平生意。
鄉親蘇小,定應笑我非計。
才見一抹斜陽,半堤香草,頓惹清愁起。
羅襪音塵何處覓,渺渺予懷孤寄。
怨去吹簫,狂來說劍,兩樣消魂味。
兩般春夢,櫓聲盪入雲水。
──《懷人館詞》
癸酉
惜秋華
〈癸酉初秋,汪小竹水部齋中,見秋花有感,一一賦之,凡七闋,棄稿敗篋中,已十一年矣。茲補存其三闋,以不沒當年幽緒云。〉
瑟瑟輕寒,正珠簾曉卷,秋心淒緊。瘦蝶不來,飄零一天宮粉。莫令真個敲殘,留傍取玉妝台近。窺鏡乍無人,一笑平添幽韻。
芳訊寄應準。待穿來弱線,似玲瓏情分。移鳳褥,欹寶枕,露幹香潤。秋人夢裏相逢,記欲墮又還黏鬢。醒醒,海棠邊慰他涼靚。〈〔上詠玉簪〕〉
──《小奢摩詞》
減蘭
闌干斜倚,碧琉璃樣輕花綴。慘綠模糊,瑟瑟涼痕欲暈初。
秋期此度,秋星淡到無尋處。宿露休搓,恐是天孫別淚多。
〈〔上詠牽牛〕〉
──《小奢摩詞》
露華
一痕輕軟,愛盡日沈沈,禪榻香滿。別樣瓏鬆,小擘露華猶泫。斜排玉柱停勻,握處兜羅難辨。幽佳地,龍涎罷燒,銀葉微暖。
空空妙手親按。是金粟如來,好相曾現。祗樹天花,一種莊嚴誰見?想因特地拈花,悟出真如不染。維摩室,茶甌經卷且伴。〈〔上詠佛手〕〉
──《小奢摩詞》
金縷曲 (癸酉秋出都述懷有賦)
我又南行矣!笑今年鸞飄鳳泊,情懷何似?縱使文章驚海內,紙上蒼生而已,似春水幹卿何事?暮雨忽來鴻雁杳,莽關山一派秋聲裏。催客去,去如水。
華年心緒從頭理。也何聊看潮走馬,廣陵吳市?願得黃金三百萬,交盡美人名士,更結盡燕邯俠子。來歲長安春事早,勸杏花斷莫相思死。木葉怨,罷論起。
〈店壁上有「一騎南飛」四字,為《滿江紅》起句。成如幹首,名之曰《木葉詞》,一時和者甚眾,故及之。〉
──《懷人館詞》
甲戌
湘月 (甲戌春,泛舟西湖賦此)
湖雲如夢,記前年此地,垂楊係馬。一抹春山螺子黛,對我輕顰姚冶。蘇小魂香,錢王氣短,俊筆連朝寫。鄉邦如此,幾人名姓傳者?
平生沈俊如儂,前賢倘作,有臂和誰把?問取山靈[2]渾不語,且自徘徊其下。幽草黏天,綠陰送客,冉冉將初夏。流光容易,暫時著意瀟灑。
〈右《懷人館詞》一卷,原集凡九十闋,辛巳春日選錄三十二首,癸未六月付刊。〉
──《懷人館詞》
乙亥
摸魚兒 (乙亥六月留別新安作)
者溟濛江雲嶽雨,是誰招我來住?空桑三宿猶生戀,何況三年吟緒?來又去,可題遍蓮花六六峰頭路?幽懷更苦。問官閣梅花〈(郡齋梅花三十樹,皆余手植。)〉,誰家公子,來詠斷魂句?
眠餐好,多謝瀕行囑咐。吾家有妹工賦〈(予有妹嫁新安。)〉。相思咫尺江關耳,切莫悲歡自訴。君信否?只我已年來習氣消花絮。詞章不作。倘絕業成時,年華尚早,聽我壯哉語。
──《懷人館詞》
賣花聲 (舟過白門有紀)
帆飽秣陵煙,回首依然,紅牆西去小長幹。好個當壚人十五,春滿壚邊。
如此六朝山,消此鴉鬟,雨花雲葉太闌珊。百里江聲流夢去,重到何年?
──《懷人館詞》
丙子
百字令(蘇州晤歸夫人佩珊,索題其集)
揚帆十日,正天風吹綠江南萬樹。
遙望靈巖山下氣,識有仙才人住。
一代詞清,十年心折,閨閣無前古。
蘭霏玉映,風神消我塵土。
人生才命相妨,男兒女士,歷歷俱堪數。
眼底雲萍才合處,又道傷心羈旅〈(夫人頻年客蘇州,頗抱身世之感。)〉。
南國評花,西州吊舊,東海趨庭去〈(予小子住段氏——按指段玉裁——枝園,將之海上省侍,故及之。)〉。
紅妝白也,逢人誇說親睹〈(夫人適李,有李青蓮之目。)〉。
附:答龔璱人公子,即和原韻(歸懋儀〈歸佩珊〉)
萍蹤巧合,感知音得見風前瓊樹。
為語青青江上柳,好把蘭橈留住。
奇氣拿雲,清談滾雪,懷抱空今古。
緣深文字,青霞不隔泥土。
更羨國士無雙,名姝絕世〈(謂吉雲夫人。)〉,仙侶劉樊數。
一面三生真有幸,不枉頻年羈旅。〈(時尊甫備兵海上,公子以省覲過吳中。)〉
繡幕論心,玉臺問字,料理吾鄉去。
海東雲起,十光五色爭睹。
──《懷人館詞》
摸魚兒 (鈕布衣話東西兩湖洞庭之勝,並出示《山中探梅卷子》,因題)
數東南千巖萬壑,君家第一奇秀。雪消縹緲峰巒下,閑鎖春寒十畝。春乍漏,有樵笛來時,報道燕支透。花肥雪瘦。向寂寂空青,潺潺古碧,鐵幹夜龍吼。
幽人喜,扶杖欣然而走。酒神今日完否?山妻妝罷渾無事,供佛瓶中空久。枝在手,好贈□蘆簾,紙閣歸來守。寒圖寫就。看畫稿奴偷,詞腔婢倚,清夢不僝。
──《懷人館詞》
百字令(投袁大琴南)
深情似海,問相逢初度,是何年紀〈(乃十二歲時情事。)〉?依約而今還記取,不是前生夙世。放學花前,題詩石上,春水園亭裏。逢君一笑,人間無此歡喜。
無奈蒼狗看雲,紅羊數劫,惘惘休提起!客氣漸多真氣少,汩沒心靈何已[3]?千古聲名,百年擔負,事事違初意。心頭閣住,兒時那種情味。
──《懷人館詞》
丁丑
金縷曲 (贈李生)
海上雲萍遇。笑頻年開樽說劍,登樓選賦。十萬狂花如夢寐,夢裏花還如霧。問醒眼看時何許?儂已獨醒醒不慣,悔黃金何不教歌舞?明月外,思清苦。
奇才未必天俱妒?隻君家通眉長爪,偶然仙去。花月湖山驕冶甚,一種三生誰付?衹片語告君休怒。收拾狂名須趁早,鬢星星、漸近中年路。容傍我,佛燈住。
──《懷人館詞》
虞美人
〈陸丈秀農杜絕人事,移居城東之一粟庵,暇日以綠綃梅花帳額索書,因題詞其上。〉
江湖聽雨歸來客,手剪吳淞碧。笛聲叫起倦魂時,飛過蒙蒙香雪一千枝。
少年多少熏蘭麝,金鳳釵梁掛。年來我但寫《蓮經》,要伴荒庵一粟夜燈青。
──《懷人館詞》
減蘭
〈偶檢叢紙中,得花瓣一包,紙背細書辛幼安「更能消幾番風雨」一闋,乃是京師憫忠寺海棠花,戊辰暮春所戲為也,泫然得句。〉
人天無據,被儂留得香魂住。如夢如煙,枝上花開又十年。
十年千里,風痕雨點爛斑裏。莫怪憐他,身世依然是落花。
校勘記
[1]此闋寫作時間不可考,據題記及其在《懷人館詞》中的前後詞,疑作於1812年舉家出都赴安徽途中。
[2]《四部叢刊》吳刻本為「靈山」,此據《龔定庵全集類編》和上海人民版《全集》改為「山靈」。
[3]《四部叢刊》載此句為「汩投心靈何已」,此據《龔定庵全集類編》和上海人民版《全集》改。
本站仅提供存储服务,所有内容均由用户发布,如发现有害或侵权内容,请点击举报。实盘杠杆平台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


